三年级学生理解和倍、差倍关系的教学实验与研究
发表时间:2011-06-09 阅读次数: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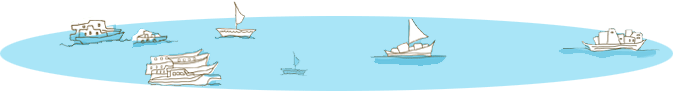
在新课程改革与实验中,相比较而言,对于应用问题(即传统的应用题)的讨论与研究是比较多的,从教学目标和存在形态的变化到教学内容与学习方式的改进等等。本文试图以三年级学生理解和倍、差倍关系的实验研究为例,以图形等式表征应用问题的数量关系,通过图形等式推算获得问题的解决,通过从同构异素的问题情境中概括出相同的数学结构模式,增进学生对应用问题特征的理解,并以此降低应用问题学习的难度,培养学生的代数思维能力。
为了方便表达,对本文涉及的应用问题的类型与相关术语作一些解释说明。如以下3个应用问题:
问题1 食堂做肉包子80个,做菜包子的数量是肉包子的3倍。肉包子和菜包子一共做了多少个?
问题2 食堂共做肉包子和菜包子共320个,菜包子的数量是肉包子的3倍。肉包子和菜包子各做了多少个?
问题3 食堂共做菜包子比肉包子多160个,菜包子的数量是肉包子的3倍。肉包子和菜包子各做了多少个?
上面3个应用问题的基本数量关系都可以概括为“1份数×(倍数±1)=几份数”。其中问题1是先求倍,再求和,即求倍求和问题。把求倍求和问题进行可逆性变换,就得到问题2,这种类型称为和倍问题。问题3是差倍问题。
在两步计算的应用问题中,求倍求和问题是重要的类型,而和倍、差倍问题则因为“比较难”,没有进入到传统教材中作为一般学习的要求。但是,和倍、差倍问题的数学结构模式存在于一般的分数应用问题与比例应用问题之中,如以下两个应用问题:
问题4 食堂做肉包子和菜包子共320个,肉包子的数量是菜包子的13。菜包子做了多少个?
问题5 食堂做肉包子和菜包子共320个,肉包子与菜包子的数量比是1∶3。菜包子做了多少个?
这也就是说,学生在学习整数应用题时,是不涉及和倍、差倍问题的,但是在学习分数或比例应用问题时,则需要重新构建和倍、差倍的数学结构模式,这是一个“系统漏洞”。如果在整数应用问题的学习阶段,构建起和倍、差倍问题的数学结构模式,打上“系统漏洞的补丁”,不仅可以使教材前后知识的逻辑关系更加严密,而且有利于学生沟通此类分数、比例应用问题与整数应用问题的本质联系,这对于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都是比较有益的。
我们的实验与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核心的问题进行:知识如何在教材中呈现?学生以怎样的方式学习?三年级学生理解和倍、差倍关系的水平怎样?
如前所述,求倍求和问题的可逆变换就是和倍问题,把和倍问题和的表述句转化为差的表述句,就是差倍问题。这些数学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学生学习的重要资源。因此,在教材中,我们把求倍求和问题与和倍问题一并呈现,以题组的方式设计在教材中,通过求倍求和问题的解决,使学生熟悉数量之间的关系,让学生经历把问题变成条件,把条件变成问题的变换过程,感受新知识与已有知识之间的联系。差倍问题与和倍问题的结构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已知几份数(和倍问题的几份数是两个数量的和,差倍问题的几份数是两个数量的差)、两个数量的倍数关系,求1份数。进一步,把这个数学结构以正向的数量关系表达,可以概括为“1份数×(倍数±1)=几份数”,这样和倍问题就与求倍求和(差)问题统一起来了。
对于这些知识内在联系的梳理与数学结构模式的概括,直接导致教学思路的变化,并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方式。概括地说,改变了以往“一课一例”的教学模式,突出了以数学结构模式的理解与把握为基础,强调通过数量关系的变换沟通不同类型之间的内在关联,这可以看作是应用问题教学改革的重要探索。具体的说,就是用图形来代替未知的数量,把和倍、差倍问题的数量关系以图形等式表征,使得一个逆向的数量关系得以正向的表达,不仅使得学生在解决和倍、差倍问题时构建等量关系的思维过程变得简单,而且与已有的知识(求倍求和)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使得求倍求和问题的学习成为和倍问题学习的重要知识与经验基础。举例说,如问题2的数量关系分析,通常都要借助于画线段图,根据“菜包子的数量是肉包子的3倍”,把肉包子表示成1份,菜包子就是这样的3份,总共是4份,与320个相对应。把320除以4就可以求出每一份的数量。以图形等式表征数量关系,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路径,如用▲表示肉包子的个数,菜包子的个数可以用“▲ ×3”表示,其数量关系可以表征为▲ ×(3+1)=320。当然,这里强调用图形等式表征数量关系,并不排斥用线段图表征数量关系的方式,相反,在教学的起始阶段,可能要用线段图表征数量关系作为学生理解用图形等式表征数量关系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两者在学生不同的学习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教学价值,前者对于对应关系的表征更加直接明晰,后者对于把握数学结构模式、培养代数思维能力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当然,用图形等式推算的方法解决问题,图形等式推算方法的学习与技能训练是需要构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作为一种计算训练的形式,本身有着重要的教学价值,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图形等式表征数量关系,可以是个性化的、多元化的,认识不同表征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提升学生数学理解的重要部分。如问题2的表征,除了前面提到的▲ ×(3+1)=320之外,还可以是▲ ×3+▲ =320。如果用两个图形分别表示不同的数量,则表征的方式更为多元,如▲ ×3=■,■ +▲ =320;■ ÷3=▲,■ +▲ =320;■ ÷▲ =3,■ +▲=320等等。其中两个图形两个等式的表征,可以通过式与式之间的关系,把■用“▲ ×3”来代替,从而转化为一个图形一个等式的表征。这个转化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化归的数学思想方法,而且通过转化沟通了不同表征之间的联系,使学生对于数学结构模式的理解更加丰富和深入。
对于学生理解和倍、差倍问题的实验与研究,我们在2010年6月选择了普通学校三年级2个班74名学生进行调查实验。我们先对调查对象施行和倍、差倍关系的图形等式推算与相关的解决问题的教学,安排两节课进行。第一节课主要学习图形等式推算的方法,在模式直观中理解和倍、差倍的数学结构,熟悉和倍、差倍问题不同的表征形式及其相互之间的转化关系。第二节课主要学习用图形等式推算的方法解答和倍、差倍问题。其基本思路是,用线段图的直观表征一份数与几份数之间的关系,以提出求倍求和的两步计算应用问题为起点,让学生初步感知和倍、差倍问题中数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数量关系的可逆变换生成和倍问题,再以图形等式表征其数量关系并通过图形等式推算获得问题的解决。教学中,让学生经历两次概括提高学生对数量关系的概括和理解水平。一次是比较和倍与差倍相同点和不同点,理解这类问题的结构特征,建立倍数与几份数之间对应的观念;另一次是让学生发现同构异素的问题情境中都包含相同的数量关系。
在教学了和倍、差倍的图形等式推算后,我们进行了后测,统计发现学生的平均通过率为77.5%,其中一种图形一个等式推算的掌握较好,通过率是88.1%,而两种图形两个等式的推算通过率只有66.9%。根据学生掌握的实际情况,第二天,我们安排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行专项训练,主要教学把两个图形等式转化为一个图形等式的思考过程,之后再次进行测试,使平均通过率达到85.6%.在学生基本掌握了图形等式推算的方法之后,我们教学了用图形等式推算的方法解答和倍、差倍问题。上完课之后立即对学生进行后测。后测分为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用图形等式推算的方法解答简单的和倍、差倍问题,主要考查学生解题的基本方法与技能。另一部分是从算术方法表征与图形等式表征的和倍问题中选择其中的一个进行编题,主要考查学生对于结构模式的把握能力。对于前一部分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学生用图形等式解答和倍、差倍问题通过率是87.8%,其中89.1%的学生能较好的使用图形等式推算的方法正确地解题。8.1%的学生掌握较差,在没有个别指导的情况下,几乎不能解决任何一道题(后与课任教师交流得知,这几名学生的数学基础和理解比较差,解答应用题很困难),而且不同的学生选择图形等式表征有不同的偏好,18.9%的学生选择用两个图形两个等式表征数量关系,70.3%的学生选择用一个图形一个等式表征数量关系,这两类学生解题的成功率相差无几。72.9%的学生选择用图形等式的表征来编题,不考虑语言的逻辑性,学生编题的正确率高达92.5%,这说明学生对于这类问题的结构特征有较好的掌握。
上述测试结果表明,三年级学生对于和倍、差倍问题的理解水平较好,用图形等式推算的方法解答和倍、差倍问题是可行的,而且学生运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问题的结构特征有较好的把握。
由于实验只是强化用图形等式推算的方法解决和倍、差倍问题,因此还有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以下几个问题尚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实验获得 详实的数据。如用图形等式推算与其它方法教学和倍、差倍问题差异性的比较研究,图形等式推算训练对于学生理解应用问题的数学结构模式的影响研究,重视数学结构模式的应用问题教学效果的研究等等。相信,随着这些研究的跟进,应用问题教学改革的思路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